伯恩斯坦钢琴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2013/1/23 15:01:04www.cn010w.com点击:7098次
伯恩斯坦--钢琴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伯恩斯坦--钢琴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伯恩斯坦似乎和一种鲜红的颜色永远联系在一起,鲜 红的外套、雪白的头发,形成极强烈的反差。尽管伯恩斯坦不会穿着鲜红的礼服上台,但红色似乎成了他永远的象征。它意味着激情、诗意、泛滥的浪漫和隐含在微笑中的睿智的幽默与俏皮。 伯恩斯坦(1918---1990)
新大陆的音乐巨人
在20世纪中叶后崛起的指挥大师中,如果说卡扬是欧洲古典乐坛的帝王,那么伯恩斯坦便是北美这块新大陆的最高权威。正是伯恩斯坦的出现,使得北美这块新大陆有了足以与大西洋彼岸的古老欧洲抗衡的音乐代言人。
指挥艺术不仅是伯恩斯坦音乐天才的最佳用武之地,也是他艺术个性的最典型体现。他一方面将古典音乐的精神遗产与新大陆所孕育的旺盛的生命力融为一体,将浪漫主义的阐释风格推到了极致,同时又不断地从深厚的欧洲传统中汲取精神营养,寻找音乐上的精神归宿。
这种指挥风格并非在所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都能取得成功。像当代绝大多数指挥家一样,贝多芬的作品在伯恩斯坦的指挥曲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某些重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场合,伯恩斯坦是以贝多芬作品在当代的最佳阐释者之一的形象出现的。如在1970年纪念贝多芬诞辰200周年之际,奥地利政府选定伯恩斯坦在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菲岱里奥》;1989年圣诞节,为庆祝柏林墙的拆倒,伯恩斯坦指挥了第九交响曲。他先后为CBS公司和DG公司各录制了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后一套是在贝多芬的主要居住城市维也纳与作为音乐传统化身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录制的,但在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格看来,伯恩斯坦对贝多芬交响曲中的阐释“才华多于趣味”。 伯恩斯坦气质中过于浪漫化、主观化的成分使他缺少贝多芬作品所要求的均衡感及自我约束能力。当然,第三《英雄》交响曲是一个优秀的例外,伯恩斯坦对这部交响曲的阐释无疑属于最杰出之列,在这里,伯恩斯坦的音乐理解力,他的充沛的热情以及对纪念碑式宏伟气概的追求使他真正捕捉到了贝多芬精神的核心。
与伯恩斯坦的指挥风格不能契合的另一位作曲家是布鲁克纳。伯恩斯坦浪漫的指挥风格照理应该适合这位晚期浪漫派作曲大师那些内涵丰富、精神境界宏大的交响曲,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伯恩斯坦很少指挥布鲁克纳的作品,只是对第九交响曲情有独钟,先后留下了两个录音。理查德*奥斯本在听过后一个也就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DG公司录制的版本后作也的评价很有代表性:“我认为伯恩斯坦热爱这部作品但不理解它。”另一位评论家劳伦斯*B*约翰逊指出,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意味着某种精神企求,这种企求在伯恩斯坦指挥的马勒作品中意味斗争。然而在布鲁克纳作品中并没有斗争,有的只是渴望与人性,以及对上帝的赞美。”
这各情况的根源在于新大陆的文化与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差异。约翰*L*霍尔姆斯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唱片是的指挥家》一书中这样概括伯恩斯坦的指挥成就:“伯恩斯坦是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最有造诣的美国指挥家,他多方面的才华及音乐修养必须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他在伟大的指挥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却仍是一个问题。对于世界是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伯恩斯坦身上体现了美国文化的许多为人们熟悉的特征:过分展现的魅力与光彩,感情是自我约束的缺乏使得他难以将热情与夸张的渲染区分开来。”
然而,伯恩斯坦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国文化特征以及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激情澎湃、丰富复杂的指挥风格,这种风格在海顿、马勒、斯特拉文斯基中得到了最充分发挥。这三位作曲家分别属于古典、浪漫和现代时期,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正如伯恩斯坦本人认识到的那样,他们三人都可以被看作是最细腻的民间音乐家,也就是说,他们都将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民间音乐传统,将民间音乐素材纳入到高度发达艺术的语言中,同时又不失却民间音乐朴素自然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伯恩斯坦音乐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民间”一词有着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远为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它就本质而言是指人民和大众。正如戴维*希夫深刻断言的:“他们(指伯恩斯坦)相信公众。音乐是为大众、为所有人创作的,而不是为了音乐家和少数有教养的音乐会听众创作的。音乐喜剧是对公众说话的、戏剧、电影和电视是能触及到亿万人民的媒体-‘亿万人民’,这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合唱队唱出的词汇,是伯恩斯坦的信条。”伯恩斯坦从海顿、马勒、斯特拉文斯基中寻找到的是过去与现在、经典与大众以及不同文化间在精神上的沟通、融合。评论家戴维*赫维茨在美国《CD评论》杂志1993年7月号上评论索尼唱片公司在“皇家版”系列中重新发行的伯恩斯坦指挥海顿交响曲录音(“巴黎”和“伦敦”交响曲)时认为:“伯恩斯坦”是一位最大的海顿作品指挥家。就象在马勒作品中一样,海顿的音乐中的某些东西与这位指挥家的气质相契合。事实上,海顿与马勒也颇有共同之处。在音乐上他们都体现了兼收并蓄的特征,将巴罗克时代的对位技巧与民间曲调、乡村舞曲及进行曲轻而易举地融为一炉。两位作曲家都是配器艺术的积极革新者,二人都有极为丰富的幽默感(这一点在马勒的作品中经常被忽视,而在海顿的作品中又常被误解)。所有的这一切在伯恩斯坦的阐释中都有鲜明的呈现,不过,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演奏中包含的巨大的活力。”伯恩斯坦将海顿完全变成了当代人心目中的海顿这种阐释与那种回归历史的本真演奏或古乐运动格格不入。古乐器运动倡导者们用完全或尽量贴近海顿时代的乐队规模、表现手法和感情将音乐和听众拉回到过去,而伯恩斯坦则完全以现代人的眼光、要求、热情和理解力,用庞大的现代管弦乐队将海顿音乐中的力量和美、热情和幽默表达的淋漓尽致。新大陆音乐巨人的充沛活力与热情并没有被欧洲十八世纪宫庭的繁文褥节所束缚,相反,旧式的小步舞那种拘谨平缓的舞步被新大陆崛起的现代人潇洒豪迈的步伐取代。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伯恩斯坦在海顿作品阐释上的成功反映了新的土地、新的民族以及新的时代所具有的力量和自信。当代最杰出的海顿研究权威H.C.宾汉*兰登断言:“伯恩斯坦即使不是我们今日拥有的海顿音乐的最伟大的阐释者,也是最伟大的之一,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
在马勒作品阐释上伯恩斯坦完全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已经成了马勒精神的化身。
与海顿相比,马勒的个性和精神世界与伯恩斯坦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马勒精神世界中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伯恩斯坦精神中也有着对应和共鸣:创造者与阐释者,犹太教与基督教信念,信仰与怀疑,天真与世故……伯恩斯坦的阐释突出和强化了马勒精神世界中的对立与矛盾,使马勒的作品真正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写照。正是与马勒精神的这种天然契合,使伯恩斯坦成为马勒音乐在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阐释者。
像马勒一样,伯恩斯坦也融指挥才能与作曲才华于一身。这种情况自近代指挥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起并不多见。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体现了伟大的古典-浪漫传统在其即将走向终结时辉煌的回光反照,而伯恩斯坦则显示了新大陆在音乐上拥有的巨大潜能。他以自己用之不竭的热情与精力将音乐带给亿万大众。
伯恩斯坦生平大事年表
1918年8月25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
1928年拥有生平第一架钢琴,生活从此转变,并开始尝试作曲。
1932年师从海伦*柯兹学钢琴。海伦*柯兹自1944年开始成为其忠实的秘书。
1935年伯恩斯坦以优异的成绩自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同年入哈佛大学学习。
1936年师从海因利希*盖普哈德学习钢琴。
1939年4月首次以指挥身份亮相,指挥阿里斯托芬《群岛》的间场音乐。
1941年入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赖纳学习。
1943年在波士顿汤戈伍德暑期学校学习,成为库谢维茨的助手,并被罗津斯基推 荐入纽约爱乐作为助理指挥。
1943年11月15日由于布鲁诺*瓦尔特急病,伯恩斯坦上场救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指挥演出舒曼《曼弗雷德序曲》,瓦格纳《纽伦堡工匠歌手》序曲等曲目,一夜成名,获巨大成功。《纽约时报》称赞说其成功是一个真正的“美国梦”。同年其重要作品:七周年钢琴独奏;钢琴与女声独唱《我恨音乐》、《五首儿歌》完成。
1953年首次作为正式歌剧指挥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出凯鲁比尼的《美狄亚》,玛丽亚*卡拉斯主唱。并为卡拉斯再次赴斯卡拉歌剧院指挥《梦游女》。
1954年在威尼斯剧院指挥为伊萨克*斯特恩所写的作品《幽》。
1955年为王尔德《莎乐美》所谱曲了完成。
1956年《天真汉》及其序曲完成。
1957至1958年被聘为纽约爱乐乐团联合首席指挥,1958-1969年为该乐队的唯一指挥,是第一位任此职的美国人。完成《西部故事》。
1958年《初生》完成,此音乐为克里斯托夫*弗德所著剧本而作。
1959年率纽约乐团访苏,晤见肖斯塔科维奇、阿什肯纳济、科冈、哈恰图良、帕斯捷尔纳克等。同年出版《乐(yue)趣》,访苏之后环欧巡演,举办了五十场音乐会。
1962至1963年第二部著作《青年音乐会的听与读》,第三部《音乐之无穷多样性》。
1963年第三交响曲完成。
1964年首次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指挥演出。
1965年《Chichester赞歌》完成。
1966年在维也纳首演。
1969年成为纽约爱乐的“终身桂冠指挥”。
1970年经年之后再访维也纳,为纪念贝多芬诞辰二百周年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菲岱里奥》。
1971年9月8日伯恩斯坦的《弥撒》首演开始,其作品在德国被大量上演。
1974年指挥两怀念库谢维茨基的音乐会,一场在汤戈伍德,一场在纽约中央公园。
1976年印第安纳州的巴特勒大学,首次举办了“伯恩斯坦周”。
1983年再次赴欧指挥。
1990年10月14日去世。
伯恩斯坦--钢琴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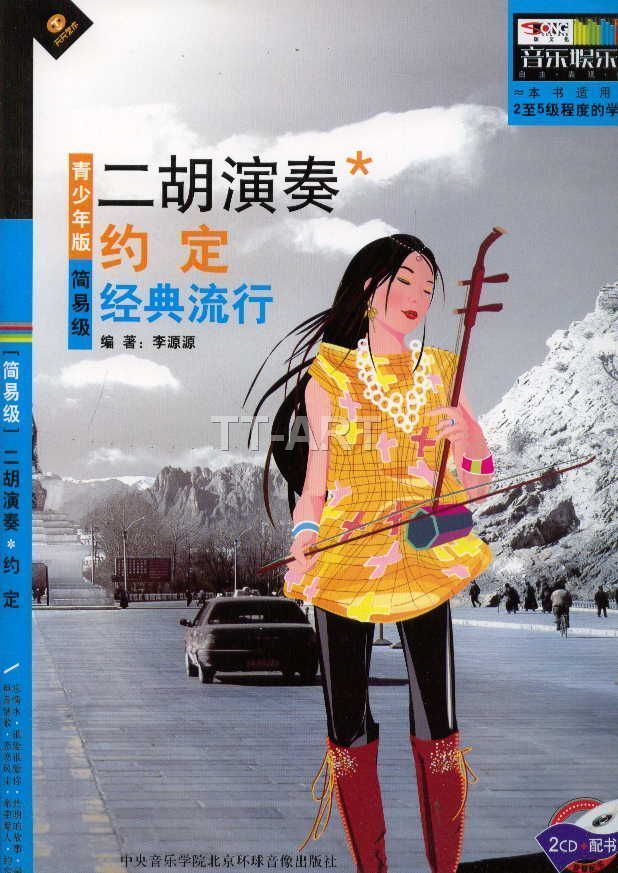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20200171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202001714号